某省2015年度教育考試用文化用品采購項目采用公開招標方式進行采購。采購人為省教育局,采購內容為2015年度采購人管轄范圍內學校某考試用文化用品,采購數量為13萬套,采購預算價為22元/套,項目總金額為286萬元。該項目關于投標人的資格條件為:具有獨立法人資格,注冊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文化用品制造廠家;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設備和專業技術能力;具有依法納稅和社會保障資金的良好記錄;參加本次政府采購活動的前三年內,在經營活動中沒有重大違法記錄;不接受聯合體投標,不接受代理商投標。
2015年2月,該項目如期開標,共5家文化用品生產企業提交了投標文件,并分別通過了初步評審(資格性檢查和符合性檢查)。在詳細評審階段,評標專家在商務評分時發現,投標人甲公司的業績僅能滿足基本得分要求。雖然其提供了多項與本項目類似業績的中標通知書、合同文件、驗收文件的原件,但僅提供了一項對應業績的銷售發票原件(開票時間為2015年1月)。招標文件評標標準明確,“業績評分以中標通知書、合同文件、驗收文件、銷售發票4原件為準”故其其只能得基本分。后甲公司澄清稱,該企業近期面臨上市,2014年12月以前的財務賬本需提供給上市輔導機構,使用時間恰好與本項目開標時間重合,其投標文件中已提供了相關業績銷售發票的復印件,并以書面情況作出了說明。
針對這一情況,有評標專家提出,甲公司為國內文化用品一線知名生產企業,投標文件中提供的經審計的財務報表顯示,近3年該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年平均超過5億元,具有中標通知書、合同文件、驗收文件3原件的業績證明可信度;甲公司以書面形式作出說明,因上市原因造成銷售發票原件未提供的解釋具有合理性,無銷售發票原件應視為細微偏差,故甲供應商的業績分應給予滿分。不過,大部分評標專家認為,“4原件計分”是招標文件明確的規定,而且招標文件還要求評標委員會只能在招標文件中規定的范圍內進行評審,否則可能“惹火上身”。基于此,評標委員會在業績評分上僅給予了甲方基本分。
在技術評分環節,針對5家投標人的樣品進行評分,經評標委員會比較,甲公司提供的樣品從外觀、包裝、品質等方面明顯優于其他4家投標人提供的樣品。但鑒于本項目評分中業績分權重相對較大、樣品分權重相對較小,加之業績分滿分的乙公司為中小企業,其在價格評審時享有3%-6%的評分優惠,甲公司很可能失去中標資格。因此,又有評標專家提議,商務評分時應對甲公司的業績予以認可,并提醒其他評標專家評標結果可能面臨“低質高價”。但鑒于招標文件對業績評分“4原件”的硬性規定,評標委員會依然未采信。最終,乙公司以總評分0.3分的微弱優勢、高于甲公司近20萬元的價格中標。
事實上,上述案例并非個案。該項目的招標采購過程中,當部分評標專家反復提出異議時,評標委員會在剛性的評標規則面前,眼睜睜地看著乙公司“低質高價”中標,這也引發了筆者多年來的一個思考:當前,政府采購評標專家的自由裁量權究竟是大還是小?人們往往認為,除客觀分外,評標專家在評審打分環節享有較多自由裁量權,專家的自由裁量權也較難約束,因此,不少供應商處心積慮要“攻陷”評標專家。理論上講,如果評標專家的自由裁量權足夠大,相信任何一位理智、公正的評標專家都會選擇甲公司而非乙公司的產品,
那么,甲公司的書面說明情況很可能被采信,該項目的評審結果也很可能是另一種情況。
關于評標委員會的權利、職責,《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第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評標委員會、競爭性談判小組或者詢價小組成員應當按照客觀、公正、審慎的原則,根據采購文件規定的評審程序、評審方法和評審標準進行獨立評審。其第七十五條第一款規定,政府采購評審專家未按照采購文件規定的評審程序、評審方法和評審標準進行獨立評審或者泄露評審文件、評審情況的,由財政部門給予警告,并處2000元以上2萬元以下的罰款;影響中標、成交結果的,處2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禁止其參加政府采購評審活動。
政府采購工程采用了招標投標方式的,適用《招標投標法》。而《招標投標法》第四十條第一款也規定,評標委員會應當按照招標文件確定的評標標準和方法,對投標文件進行評審和比較。《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款明確,評標委員會成員應當依照招標投標法和本條例的規定,按照招標文件規定的評標標準和方法,客觀、公正地對投標文件提出評審意見。招標文件沒有規定的評標標準和方法不得作為評標的依據。其第七十一條也提出了相關法律責任。
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現行《政府采購法》《招標投標法》兩大法律體系都規定,評標專家只能按照招標文件事先規定的評標標準和方法進行評標。但是,應注意到,評標專家掌握著“公法”賦予的項目評審、否決某一投標甚至所有投標、推薦中標候選人的“生殺大權”,而評標標準和方法事先的規定,在很大程度上又往往成了評標專家免責的“護身符”。招標采購實踐中,面對紛繁復雜的評標現場、可能發生的各種意外情況,評標專家根據“一刀切”的招標文件難以作出最為合理的決定,對評標專家賦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很有必要。
再進一步說,一方面,《政府采購法》《招標投標法》兩大法律體系對程序性規定較多,對評審結果規定較少,這也契合了不少評標專家“來了就想走”“拿錢就完事”“誰中標與我無關,反正規則又不是我制定的”的想法。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法規對評標專家問責、追責的規定欠缺,招標采購活動中,買方往往通過各種舉措擴大競爭,希望達到低價擇優選擇賣方的目的,卻不得不面對價高質次的評審結果;招標采購作為市場資源配置的一種有效方式,卻難以規避“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看,筆者認為,作為專業第三方的評標專家,應當被賦予更大的自由裁量權,確保其獨立、客觀、公正、審慎地完成評審工作,從而維護招標采購市場秩序,真正選出符合物有所值價值目標的中標、成交供應商。與此相對應,還應及時出臺評標專家的責任追究機制,讓制度建設的完善與采購實踐的規范并肩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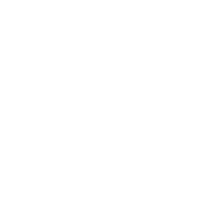 首頁
首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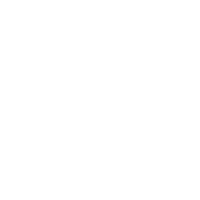 信息公開
信息公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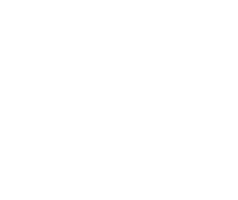 對接網絡
對接網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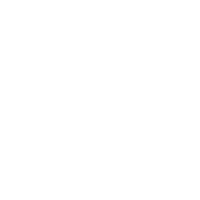 增值服務
增值服務 交易智庫
交易智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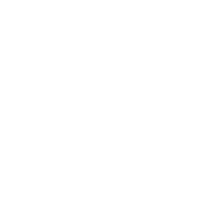 CA互認
CA互認 行業公示
行業公示


